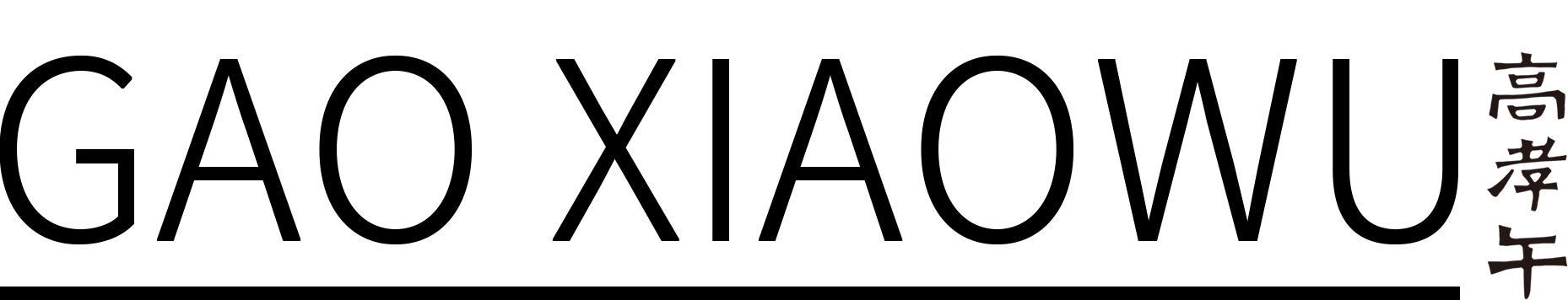艺术史学者 赵斯亮
2024年,中国当代艺术家高孝午在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展出了他的最新作品《未来标准》(又名:陌生人),延续高孝午“标准时代”系列雕塑作品的脉络,此次展出还融入了他更多元的先锋性艺术实践活动。《未来标准》不仅是高孝午对20年来“标准时代”系列演绎升华的总结,也恰好成为了中国当代具象雕塑呼应全球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缩影——1980年,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乔治·巴塞利兹 (Georg Baselitz)就曾带着其举起单臂的木质雕塑参加第39届威尼斯双年展,其事件标志着西方现代艺术在经历过以抽象为潮流的雕塑运动后对具象雕塑的复苏。因此,适逢其会,对高孝午的“标准时代”系列作品进行回顾和梳理,继而将其艺术观念置于多维的文化时空视角进行审视和思辨显得格外重要。
高孝午的“凡人艺术”
概而言之,高孝午用解构标准的方式,践行了一种新的艺术“标准”——凡人艺术。凡人艺术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2004年,高孝午创作了名为《标准时代》的雕塑作品,他以夸张地具象手法刻画了诙谑逗趣的哈腰鞠躬者,一经推出就名噪一时,旋即成为街头巷尾纷纷仿效的对象。毋庸置疑,二十年来,该作品已在全球范围内广受大众的喜爱,也不断被模仿乃至盗版,其数量不可胜算,攒集成“高孝午现象”。因此,《标准时代》常常被解读为全球消费主义的景观滋蔓,批评者称其为“刻奇艺术”(Kitsch)。事实上,不论对“高孝午现象”纷纭杂沓的解读,作为一名手不辍艺的艺术家,高孝午着实勤勉地在躬行实践一种与全球当代艺术圈现有“标准”若即若离的“标准”。
从表象上来看,高孝午的“凡人艺术”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形式上的“通俗性”,通常以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物象为摹本;内容上的“普世性”,往往以常人可通感的普遍现象为譬方;表达上的“夸张性”,多半以谑趣幽默的姿态造型为特征范式,这些“凡人艺术”所展现出来的表征与以西方为主导所构建的全球当代艺术体系的某些“标准”相吻合,使得对“凡人艺术”的解读通常如出一辙,然而,正如E.H.贡布里希所言:“并没有‘艺术’这回事,有的只是艺术家而已。”对“凡人艺术”的解读分析恰恰要思辨地看待被标准化的艺术概念,结合高孝午的“凡人艺术”的创作历程本身,望表知里,方能多维度地参详出“凡人艺术”的风貌与内涵。
“凡人艺术”vs“波普艺术”
对“凡人艺术”的理解看似可以轻易地被“波普艺术”等具有话语权的艺术概念所涵盖或取代,源于“凡人艺术”与“波普艺术”均试图以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来填平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鸿沟,而在全球消费主义的席卷下,不管“波普艺术”还是 “凡人艺术”都逃脱不了对"灵晕"(Aura)的消解,机械复制看似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宿命;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社会,符号的摹拟已完成了从“模仿”到“生产”再到“拟象”三个阶段的演进。正如“拟象”把艺术品变成了符号形式而非客观真实,日常符号不再与艺术符号分野,反而进入了无穷无尽的“再生产”,成为标准。
然而,“凡人艺术”与“波普艺术”的根本性关联仅因处于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产生了相似的艺术语言。高孝午的《标准时代》系列雕塑作品酝酿于千禧年前后,于2004年正式在中国北京登场,彼时的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城市化的进程倍道而进,全球化的步伐突飞猛进,消费主义的浪潮亦强劲扩散。至南向北迁移,高孝午同样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欣欣向荣、欢乐祥和,但他也直觉地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两面性:高速发展的社会背后将出现越来越多使人禁锢的“标准”,但“标准”也促使社会进入了另一个发展维度。因此,“凡人艺术”诞生之初所缔造出的艺术图式符号初看起来平凡通俗,其对“标准”的思考反而被更大范围的“标准”所吞噬——“拟象”无孔不入,大量对“凡人艺术”符号再次拙劣模仿反而成为主流,成为“高孝午现象”。“拟象”的泛滥使得对“凡人艺术”的解读几乎只能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被套上了沃霍尔式媚俗特质的帽子,参与到大众文化的狂欢;另一种则是认为其充满犬儒精神,在反讽地进行文化批判。
事实上,不同与对“波普艺术”的二元解读,即抑或“媚俗”抑或“犬儒”;“凡人艺术”的萌发更多是高孝午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思辨,高孝午无意去跟随“波普艺术”的步伐,他只是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标准,而该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开放的——“标准”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值得颂扬还是值得批判的,高孝午巧妙地悬置了这个问题,而他对所提出问题的解读方式本身也是动态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解读空间,使艺术家本人不断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思辨、同时也为公众参与讨论埋下了伏笔。站在这个角度,在探讨“标准”的“凡人艺术”恰恰呈现出“非标准艺术”的特点,而“波普艺术”反而是一种“标准艺术”,但从而也可以认识到“波普艺术”与“凡人艺术”的抑或重叠、组合,抑或离散、相逆,才是这个时代充满和谐而矛盾的吊诡景象。
全球化vs地方化
严格说来,用“波普艺术”来定义“凡人艺术”可能已不自觉地进入了一种艺术书写的标准,即当代艺术所使用的评价标准基本上全都来自于西方的艺术语言体系。中国当代艺术理论领域的失语论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使得中国的文艺评论家与理论家对如何定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无从下手。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全球化问题,从全球化的扁平理论来看,世界已经被构建成一个单一的系统,艺术语言与标准亦无处可逃。
然而,从片面“全球化”的视角来解读“凡人艺术”显然捉襟见肘,“全球在地化”应是解读其艺术语言的更恰当的分析工具,“全球化”与“地方化”既形成张力,又达到了一种混合关系。从高孝午所专注的雕塑艺术来看,中国早期的具象雕塑艺术与西方的雕塑风格大相径庭,中国雕塑崇尚的是表现、写意,追求气韵,而西方的雕塑趋于重现、模仿、追求神态写实。高孝午对中西雕塑的异同都了然于胸,毕业于福建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他经过了严格雕塑训练,充分地掌握了西方雕塑造型知识;而后他又奔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进行深造,也学习了中国现代雕塑奠基人滑田友借用古代南齐谢赫的“六法”阐述西洋和中国雕刻的规律。
但在雕塑实践中的融会贯通中,高孝午并不拘泥于已掌握的雕塑技法的掌握、形式风格,他充分发挥了主观创造意识,将具有个人特点的“在地性”充分发挥。“凡人艺术”中的代表系列《标准时代》的创作母题来源于在高孝午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区福建见证社会急遽转型后对平凡人生活的冲击,高孝午将自己视为“凡人”中的一员,他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加以融入对被社会所标准化后的“凡人”共性的观察,将“凡人”的喜乐、无奈、谦恭、自嘲等等窘迫状态,提炼成经典的“高式笑容”,造型精炼简洁、大面积的简化与点睛的细节刻画相得益彰。因此,虽然“标准时代”系列展现出来的雕塑形式像是西方的,但其内核却是中国的,高孝午将着力点都放在人的精神气质上,而非追求精确的人体比例,颇有中国艺术中所蕴含的“得意而忘形”之意。
不仅如此,生长在民间传统文化深厚的福建本土,高孝午的成长过程中不自觉地受到浸淫,而后他又开始有意识地对禅宗文化进行研究,体悟到“当下即是”的生命本质。因而,他擅于捕捉“当下”的瞬间,将其提炼转化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对禅宗文化的理解,更使得高孝午有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他通过直觉意象的体验,超越了物质与意识概念层面的差别,将宇宙、世界和生命“本来面目”连为一体;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当下即是”是高孝午体验智慧的“机锋”,而“标准时代”系列作品却是他作为比喻和阐释这种智慧的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标准”一开始的立意便是辩证的、开放的,而在2024年推出的新作《未来标准》,恰恰证明了这种思考的维度和广度:高孝午将目光投向科技高度发展而将产生更多幻象的未知未来,如何定义或解读“未来标准”,甚至人类是否已在解构和重构“人”这个概念本身,高孝午对“陌生化”的未来产生诸多的思考和遐想,并通过行为艺术邀请公众参加互动和探讨,最终产生具有禅宗智慧“玄有玄无”的多重答案;此种通过艺术而产生的思辨方式也与西哲黑格尔的辩证法相通。由此证明,作为一名艺术家,高孝午在“全球在地化”的进程中充分进行了主观能动性的思考和实践,在“全球化”和“在地化”两者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
Copyleft vs Copyright
毋庸置疑,“全球化”更急遽加速了对"灵晕"的消解,机械复制使得艺术品的复制变得容易且大规模化,这个现象从高孝午的“标准时代”系列作品在全球的流行便可见一斑。事实上,复制赋予了艺术性的民主化可能,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的隔阂,也改变了大众对艺术品的审美体验,使原本静态单一的欣赏方式转变为动态多元的接受模式。“凡人艺术”的诞生和发展也印证了这个时代的变化:艺术作品从神圣殿堂走向日常生活,如同拆掉基座的雕塑作品,其功能不再是仪式化的膜拜,艺术作品原有的神圣性被稀释,而大众媒介的迅速传播更将艺术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使更多的“凡人”可接触并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建构中。
因此,“凡人艺术”的初始就伴有民主性和流行性的特质,与高孝午的创作初衷不谋而合,换言之,“凡人艺术”的欣赏者和参与者本应就是多元和广泛的。然而,在实践中,伴随着作品广泛的流传度,“凡人艺术”不免涉及到另一个领域的问题,即盗版和侵权问题。从“凡人艺术”的特点来看,“凡人艺术”之所以能贴近“凡人”,乃至延续到2024年的最新作品《未来标准》,辅以行为艺术,邀请更多的大众参与,正是作为艺术家的高孝午在创作思想上赋予其“著佐权”(Copyleft)的内核。相较于“著作权”(Copyright),“著佐权”脱胎于一种更自由的著作权观,意在鼓励公众更多的参与和分享作品。
然而,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凡人艺术”在传播中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困境。一方面,“标准时代”系列的原作有着高孝午独特创造和表达方式,具有独特的氛围、风格和表现力,而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机械复制使得艺术品的原真性受到侵蚀;另一方面泛滥于市面上的各种“标准时代”系列作品只是连机械复制都谈不上的拙劣模仿,不仅削弱了观众对艺术品的欣赏和体验,还逾越了法律对“著作权”(Copyright)的保护界限。事实上,“著作权”和“著佐权”只是对版权认识的一体两面,本质上都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创造性成果,从而激发更加平等的创造机制。即便看似更为自由的“著佐权”的本质也并非承认放弃版权,构成其两大基础条件,其一是承认著作权,其二是必须获得权利人通过许可证放弃的权利,但也必须遵守许可证的规定才能行使。
从“凡人艺术”介入了版权问题来看,也说明了其外延的广度和深度,正因“凡人艺术”具有主客观性融入社会生活的特点,才能与各行业产生碰撞,激发出各种可能性,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社会生产的一种驱动力。
雕塑艺术vs “社会雕塑”
“凡人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与时俱进地关注着时代问题。以“标准时代”系列作品为例,高孝午分别于2004年创作了《标准时代》、2008年创作了《后标准时代》2013年创作了《英式标准》,这一系列作品都延续着同一种造型图式,以雕塑的方式展现。
在所有造型艺术中,雕塑是最具有多维表现力的门类,同时也是依赖物质、媒介、技艺等因素最强的艺术样式。艺术家需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实践获得高超的能力来表达自身思想,同时,物质媒介的材质对雕塑有很强的艺术约束力,方向制约着作品的审美走向。对待雕塑作品,高孝午依然是一位严谨的当代艺术家,对艺术“标准”孜孜不倦的追求恰恰是他提出“标准”这个命题的另一个写照。而通过对不同材料的研究和把握也使他对材料本身有着不一样的见地,“标准时代”系列的初稿为泥稿、后又有玻璃钢、铸铜、铸铜着色等不同的材料,高孝午为不同的作品以及其所在的场域选择了不同的材料,而不同的材料特性也在客观上对高孝午提出技艺“标准”, 因而,高孝午在进行雕塑塑造的创作过程中,也持续对“标准”问题产生实践性思考。
2024年,在高孝午首度发布《标准时代》20年之后,他延续了对这个问题的动态思辨,将《未来标准(陌生人)》推出。在造型塑造上,高孝午沿用了“标准时代”系列的经典图式,依然是一名微笑哈腰的鞠躬人,但这次创作,他将目光投向更具有未来视野的广阔疆域中,因此,这个鞠躬人是一个未来感极强的机器人形象:头顶小天线,拥有相机镜头的双眼,感应器的鼻子、耳机线的耳朵及转轴的关节。如果说,之前的“标准时代”系列的作品主要关注的是反朴还淳的“凡人”在社会中的困惑,此次的《未来标准(陌生人)》更多关注的则是天穹寰宇中“凡人”的命运问题——在未来科技冲击下的世界,人类是否将集体被“陌生化”。正如上文所提及,在“标准时代”系列的作品演进中,高孝午对此问题的思辨一直都是带有禅宗意味的,“凡人艺术”背后蕴含的哲学思辨也具有 “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特点,展现了事物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在人机一体的未来是值得憧憬还是需要引起警醒的,这个就是高孝午所提出的问题。
可以说高孝午所希冀的回答问题的方式即是提出问题,因而,《未来标准(陌生人)》从一种雕塑作品、成为了一件在地艺术作品(Site-Specific Art),又变成了一件可以游历的装置艺术作品(installation art),再演进到辅以将“陌生人”在世界具有陌生感的地方巡游、用手电筒寻找“陌生人”等行为艺术的参与式社会活动,这个历程不但是“凡人艺术”的升华,也是其回归,高孝午将“凡人艺术”再次搁置到公共社会语境中产生新的价值诉求。从艺术史的史实考释,行为艺术发韧于20世纪60年代,与装置艺术同步生成而生,这种历史的契合并不是偶然,而是艺术发展变化后的结果。我们可以将高孝午“凡人艺术”与德国艺术家博伊斯所提出的“社会雕塑”相类比。“社会雕塑”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被社会广泛参与,它把艺术的责任扩大, 已经不再仅是为人类提供可被欣赏的艺术品,而“社会雕塑”背后蕴含的内涵则是博伊斯的观念“人生就是一件作品,生命就是艺术”,继而他推论出“人人都是艺术家”,这种人本主义的艺术概念与高孝午的“凡人艺术”不谋而合,高孝午从中国文化的脉络出发,与社会中的平凡人互动,从而寻找到平凡人寻找禅机的办法,所谓的“至人如凡”,“凡人艺术”所涵盖的外延也包含着邀请公众一同对社会议题参与讨论的行为。换言之,虽然高孝午从不以批判社会为出发点,但他着实是一位既关注艺术观念又思考社会意义的艺术家。
“凡人艺术”的演进从雕塑到社会雕塑本身也反映了“凡人艺术”在艺术的自律和他律中取得的平衡,一方面是艺术的自为存在,另一方面是艺术与社会的联系,这种“凡人艺术”背后所蕴含的双重本质不断地显现与流变于其所有艺术现象中。这种艺术实践将“整个人类关系及其社会背景作为其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Nicolas Bourriaud)也是关系美学中的核心要义。从对“版权问题”困顿的解决到对“陌生人”问题的探讨,“凡人艺术”通过艺术领域之外的关系制造来阐释艺术,从而产生了远超于艺术定义之外的特殊魅力。
标准化vs非标准化
当从艺术介入社会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凡人艺术”,那么高孝午以此为契机思考了一个颇为深刻的问题,即何为标准及人在标准下会做出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提出伴随“凡人艺术”的不断演进,在不同时空、场域、人群的变化中产生了不同的答案。
从语义学上来说,“标准”这个词本身就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其二是 “榜样、规范”,这二者都指向了逻格斯主义中传统的秩序观。我们从艺术史的维度审视来审视“艺术标准”,高孝午提出的这个问题便饶有趣味。从维伦多夫的维纳斯到红山文化的女神陶塑,从古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巨大而简洁的坐像雕塑到东汉击鼓说唱陶俑,从键陀罗艺术和佛教艺术中的石窟造像到非洲木雕和南美印第安人雕刻,每个时代都有其艺术标准。
然而,从表面上看当代艺术本身就陷入了一种“非标准”的迷雾,这是由于艺术的本质或界定的问题已发生转向,无论是艺术本质论所关心“艺术是什么”,还是艺术本体论所关心的是“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艺术作品“如何存在”的问题都向传统的、具有“标准”的艺术提出了挑战。美学家们关注艺术界定问题,形成了“否定标准”、“限定标准”和“约定标准”的不同思考。然而,吊诡的是,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解读,都不约而同地对“艺术”进行再标准化的重构。
可以说“凡人艺术”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对“艺术标准”的讨论,“凡人艺术”的边界也在发展中呈现出不断外延和内收的一个动态过程,一方面“凡人艺术”不断融入社会生活,与各领域产生碰撞,激发出各种可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驱动力;另一方面,“凡人艺术”对艺术社会化也有着理性的思考和观察,它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思辨其发展走向,警惕艺术沦为被某种“标准”操纵的工具。
进而,“凡人艺术”可以参与讨论的“标准”也是多维的——社会现实、AI科技、未来世界、自然环境、哲学体悟等等都是其可能涉及的领域。如是说,“凡人艺术”所开启的标准只是在创造一个社会沟通的契机,它既不完全是从理论或观念上解释社会,更不是为社会问题寻找一种唯一的解决方案,而是持续开启社会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不仅使艺术家对社会场域的回应, 也使艺术创作中通过观者的参与和社会互动,合力塑造“凡人艺术”的共同价值。
行文至此,想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此次在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期间,我作为“凡人艺术”观者的身份,也参与了高孝午《未来标准(陌生人)》的互动,此时我在“非标准”中对其作品进行直觉感悟;而当下我以艺评人的身份撰文,或也无法避免地将陷入“标准化”的艺术评论方式。看来关于“凡人艺术”的思辨应该不单单禁锢在文本之中,也永远应该处于文本之外。
那么,那么未来的人类到底是愈发标准,还是越发脱离标准;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思考,还是千高原上浩浩荡荡游牧着各种陌生人的凡人思考,“凡人艺术”的未来之路还在继续。
2024年4月30日·佛罗伦萨